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驾驶汽车,到十字路口时,放慢车速,看到绿灯亮起,才慢慢通过。 突然,一辆汽车发疯般的撞来… …
男人的车,被顶出去十几米,严重损毁,人也受伤。 男人忍着剧痛爬出来,右臂断裂的骨头,已经刺破皮肤,露在外面。
两个男孩路过,问那人要不要去医院? 男人摇摇头,说还有急事要办,请求一个男孩脱下衬衫,给他绑住右手。
男孩照办了。 男人拿出100美元,说这是补偿。 男孩不要,说只是帮忙,而且100美元也太多了… …
男人执意不肯,硬塞过去,然后才蹒跚离开。 一辆公交车,刚刚停下。
后面跑来一位抱着孩子的黑人,挤到一名老太太的前面,抢先上车。 后面一位有风度的男士拉住他,让他向老太太道歉。
那黑人却抓住风度男的衣领,大声说:“FUCKYOU!” 黑人的孩子,眼泪汪汪地望着窗外,因为他的玩具在追赶公交车时掉下了。 可父亲不允许他捡,他只能眼看着玩具被汽车碾碎… …
你如何评价上面两个男人? 第一个,遵守规则,坚强,为别人考虑?
第二个,不懂得礼让,粗暴、没有同情心? 可事实是怎样的?
上述两个情节,分别来自两部电影。 第一个情节出自电影《老无所依》,被撞的男人叫安东,是一名杀手。 他用手铐勒死警察,用杀牛的系簧枪射穿路人的脑袋,用散弹枪干掉自己的雇主… … 安东出车祸的地点,在一个女人家附近,这个女人刚刚被安东杀害… …
第二个情节来自《当幸福来敲门》,那父亲叫加德纳,是一名推销员。 一次决策失误,让他倾家荡产,老婆离去,他和儿子相依为命。
加德纳勤奋、聪明,正努力进入一家大型的股票经纪人公司。 他带着儿子,睡过公共厕所,睡过收容所,即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还要乐观地对待孩子,维护孩子的梦想。
为了赶上到收容所的最后一班车,加德纳顾不上繁文缛节,否则他和儿子又将露宿街头。 是否因为不熟悉,才引发偏见?
我想说明什么? 难道仅仅想表示: 一个在车祸中表现克制的人,有可能是个杀人犯?
而一个粗鲁无礼的男人,有可能是个好父亲?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们日常所接触的人与事,就如同电影中的一个桥段,我们往往根据桥段,就推演出全局,甩出一个自以为是的结论。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线上学习群。 为期30天,主要讲心理学。
群主是一个业界大V,拥趸众多,收费不菲。 期间,一名女学员想和群主私下沟通,可群主一直没回复。
于是女学员便在群里唠叨起来,说缴了这么多学费,群主还不如“siri”热情,对她的问题视而不见。 群主有点火,说:“我哪有时间一个个去回复?” 女孩马上反驳:“你课上还说,要真诚对待每一个人,你自己并没有做到啊?” 这时,群主的广大粉丝不干了,TA们开始群起围攻女孩:“缴那点儿学费就想享受一对一服务啊?” “你太自私了吧,也不为别人考虑考虑?
” “一看你就是喜欢占便宜的人……” 最终女孩落寞收场,离群而去。 那女孩的心结,我多少有点体察。
大V所讲的心理学积极正向,在女孩心中,那些道理与大V已融为一体。 大V的不理不睬,打破了这种统一。
粉丝们的反应,也不难推断,大V是我们大家的,怎能容你私自占有? 不理你是对的,你却不依不饶,只能说明你是个自私而无理取闹的人。
女孩通过桥段,定义大V就是人生导师,而忘记他另外一个经济人的身份。 众粉丝根据桥段,定义女孩是个自私鬼,TA们可能没去想,女孩其实是个热心肠,她只是太认真了,因为购买这门课程,她花了半个月的工资… …
是否因为不熟悉,才引发偏见? 朋友之间是否就可以置身于偏见之外吗?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讲了个故事: 牛书道和冯世伦本是好基友。 两人某年冬天结伴去拉煤。
一晚,离家还有50里时,牛书道车轴断了,只好露宿荒郊,等天亮再作打算。 好在两人一起有个伴。
冯世伦有点饿,就问牛书道还有没有干粮? 牛书道翻了翻口袋说:“木有了。” 半夜,冯世伦撒尿,发现牛书道竟在偷啃馒头。 心想:我陪你受冻挨饿,你却藏着口粮… …
于是,拉起自己的煤车,独自走了。 牛书道也炸了毛,心想:我翻口袋时,确实啥都没有,谁知铺被窝时,又滚出一个馒头,我总不好再说还有干粮吧?
而你却因为一个馒头,把好友撂到这荒郊野岭,太泥玛绝情了。 冯世伦通过牛世道偷吃馒头,推断对方不仗义;牛书道通过冯世伦撒手而去,推断对方太绝情; 最终两人势不两立,成为仇人。
好朋友之间绝交,常常会用一句话:“我算是看透你了!” 但是真的看透了,还是你以为看透了呢? 正如马克·吐温说的: “让我们陷入困境的,并不是无知,而是真相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 三岁以前,人看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孤立的。
以为玫瑰花和牡丹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毛巾和爸爸的区别。 我们看到地上的一摊水,那就是一摊水,而不会推断是天上的雨,还是猫咪的尿。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学会了归纳和推演。 我们知道了事物之间原来是有相似度的,所以TA们可以归为一类; 我们还知道事物之间是有因果的,所以A的存在,才导致了B的发生。
但成长并不意味成熟。 这种习得,降低了我们对事物的识别难度,提高了决策速度,节省了大脑空间。
但,坏处也随之而来: 我们根据经验,快速甩个帽子给对方,根据浮动的表象,就将本质盖棺定论。 因此,一个作者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就会被喷子下了定义:你这个人太肤浅… … 一名员工,坚持一下自我主张,会被领导下了结论:这个人不善于执行… … 一位开着日本车的司机,可能被砸爆脑袋,因为:他是个卖国贼… …
对事不要轻易下定义,对人不要随便戴帽子。 这不仅仅是对事的客观,对人的修养,更是对自我认知的重组和拓深。
越是成熟的人,越不会轻易下结论,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中,“事实推定”和“价值判断”不能混为一谈。 什么是事实推定?
我说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就是一个事实推定。 因为,就科学而言,他的贡献是可以被广泛举证的。
什么又是价值判断呢? 如果我说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人,就成了一个价值判断。
因为,“伟大的人”这个概念,在1000个人心中可能有1000个答案。 况且,爱因斯坦对妻子的粗暴,对私生女的无情,对美女的热衷,这些事实,都与“伟大的人”有所相悖。
前段时间,有个大V写了篇网络热文,里面有讲爱因斯坦和他司机故事,但其实是马克斯·普朗克和他司机的故事。 我发评论告诉他,素材采用有误,虽然对主旨影响不大,但严谨点更好。
后来,我的一篇文章,竟被那位大V留言,说到:“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多么阴暗的人……” 我说素材有误是基于“事实推定”,是可以查证的。 而他说我“阴暗”就是“价值判断”,因为“阴暗”他即证明不了,我也反驳不了。
最后只能沦为嘴官司: “你阴暗!”“我不阴暗!” “你就是阴暗!”“我怎么阴暗了?” “因为你阴暗,所以你阴暗!”“……” 你应该明白“事实推定”和“价值判断”的区别。 前者需要证明真伪,会有统一答案,需要知识与理性的共同加持; 后者却没有标尺衡量,无法用结果来论证,仅仅来源于感性的宣泄。
哪种结论更简单,更抒情、不用承担责任? 已不言而喻。
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曾这样写: 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 假如你是只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 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乘法表。
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热爱价值的领域。 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确实如此吧,我们都偏爱以“价值判断”主张自己的观点。 因为没有标准答案,谁也不能证明你错。
就像我一个朋友,他始终坚信小学应该拿“国学”取代“英语”。 就像我与第一个女朋友的分手,因为他父亲始终认为,没在国企上班的人,就不算拥有正式工作。
就像我们停不下来的辩论,到底在大城市苟且憧憬中而活? 还是在小城市舒适颓废中度日?
哪个更好? 除了用“价值判断”来为事物定性,我们更喜欢用“价值判断”为别人“下套”。
因为这不需要专业知识,人人可以表态,人人可以站队。 “那些牛鬼蛇神,活该关马棚,TA们竟敢质疑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说‘战狼2’不好看的人,肯定都没有爱国精神,没有民族气节。” “江歌案中的刘鑫,怎么能躲在屋里?怎么能不管江歌的生死?她应该冲出去,一起被捅死……” 你看,用价值判断去套牢别人是如此easy,你不用启动理性认知,你不用设身处地, 你只需眉头一皱,问到:“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当然,我并不想去挑战上述观点,因为如此,定会被喷子水漫金山,如果应战,又会陷入毫无意义的价值判断之争… …
所以,我只想说明的是: 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不要轻易下结论,因为事像存在复杂性,你不能切片化处理,如果要下结论,也要避免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应该以事实推定为基础。 你看,上面就是我下的一个结论,所以,我并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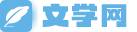 文学网
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