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杯里的水很清澈,一夜过后,还是这样。 “嘿,”墙壁上的钟表开始转动,指针扬起尘埃,“就凭你,也想变得清澈么?” 我坐在椅子上,有些犹豫。
是啊,我想这么回答,但话音稍显疲惫。 “是。”我省略了最后的字,以表明立场。
“这个目的,是纯粹的么?” 嗯? 我险些用鼻子发出这个音,好在止住了。
曾经,我也试图考虑过这点,但要么无答案,要么因有答案而选择忽略。 “是吧。”我加了最后的字,像在弹珠机前似的。
如果不是我赋予的,自然是别人了,可若是我赋予的,又怎能保证呢? 指针传来钝响,像是被一根手指扳住了。
“你不要走了,”它严肃的说,“走不远的。” “或许是,”我回答,“梦也告诉了我这个结局。” “那么果然,回去吧?” “回去?还回得去么?” “回得去啊。” “你是收了他们得贿赂吧。” 它一手掩住脸庞,眼睛溢出嬉笑,“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 敲了敲高处的玻璃面,它冲我抛出媚眼。 我要伸很长的胳膊才能碰到它,真的。
我走向一扇门,它连接另一个房间。 碎裂的珍珠从底缝散过来,被灯光射的惹眼。
原以为对面会是一片海滩,但不过是个相像的居室,椅子还侧摆着,贴合之前的位置。 我觉得这里会塌陷,像是角落里爬出裂痕,天花板落下流沙,或是被黑暗夺取光线的掌控权。
电灯开关失效了,像我对呼吸的感知一样。 如果手机在这时发来通知,我一定会被吓得丢了魂。
“咚咚——” 有敲门声响起,我的视线瞥向窗户,好像在与它们进行捉鬼游戏。 它们总是躲着我——毕竟掌握着我的某些见不得人的秘密。
是谁? 盯着浸满阴湿的门缝,我本应这样提问。
“谁?” 没有应答。 说不定没有人,我想。
可若没有人,敲门的人又是谁? 难道是我?
突然,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好像自己是一张扑克牌,正在复制品里踱来踱去。 用手扶过墙壁和地面时,它们相继消失在感受里。
我的身体失去依靠,仿佛被地狱拖着下坠。 醒来时,眼睑上漆黑一片,待睁开眼,还是这样。
要有光。 恍惚之间,我的脑海里萌生出这个念头。
“光!” 我说,但没有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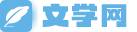 文学网
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