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趴在地图上想从密密麻麻的地点中找到我的故乡芦湾。 它过于微渺,像是沧海一粟。
在辽阔的豫东平原上和它类似的村庄棋布星罗,地图上根本没有标出它的名字。 我寻找熟悉的城镇、道路或河流作为参照,来测定它的位置。
我的手指沿着一条纤细而绵长的蓝色河流向南滑动。 那条河流是贾鲁河,人们又将它称作小黄河。
有一些史学家说它是楚汉相争时的鸿沟。 元代河防大臣贾鲁主持治理它,疏浚河道,修筑堤坝,福泽两岸百姓。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将它命名为贾鲁河。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贾鲁河发源于嵩山东麓的新密,向东北贯穿郑州,经中牟流入开封,又过尉氏至周口。
它犹如一只蓝色的千里驹在大平原上奋蹄奔腾,最后注入淮河。 我的手指在地图上抚摸着贾鲁河,它在尉氏境内与一条省道交汇,我在交汇处附近找到了故乡的位置。
我的手指停在那里,内心翻涌起一股暖流。 故乡,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微小的点,在人们心中却是一座永远难以走出的城堡。
它是我们成长的地方,不仅贮藏着我们的过去,还吞吐着我们的未来。 听老人们说芦湾从前是贾鲁河岸的一个漕运码头。
那时候河岸上停着一艘艘帆船。 芦湾出产的麻油、豆腐干与木版年画等通过这条水路运往大江南北,然而到了晚清时期由于贾鲁河堤防失修、泥沙淤积,河道渐渐壅塞不通。
河运衰落导致码头萧条,芦湾曾经舟楫云集的景象便成了南柯一梦。 到我童年的时候故乡的码头已经不复存在,河岸只留下一片荒凉残破的废墟,让人难以相信它曾经热闹繁华过。
故乡的命运因河而盛,又因河而衰,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沉浮。 我小的时候故乡没有集市,我们要跑到很远的乡镇去买东西,吃穿用行十分不便。
孩子们买新衣服要跟着父母跑跑颠颠走很远的路,我们吃不上香蕉与菠萝,我们的饭桌被萝卜、白菜、芥菜长期占据。 我们的生活纯朴而平淡,浸润河水与血汗;我们的世界好像很狭小,仅能容纳村庄与麦田。
有一年秋收之后,村民们经过多次集会商讨,决定在村头的河岸附近建造一座集市,各家各户出财出力。 大人们拿着铁锨、斧头与木锯在河岸东侧开阔的地方打桩修路,筑起商贩卖东西用的货台,又搭建起遮风避雨的顶棚。
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这项工程大功告成。 村民们高兴地庆祝,在新建的集市上搭上戏台,邀请县城的豫剧团接连唱了七天大戏。
方圆几十里的人们涌过来凑热闹。 集市上人山人海,沸反盈天。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集市上摆着一些卖棉花糖、豌豆糕和冰淇淋的小摊子,弥散出一丝丝甜美的味道。 第七天老村长站在戏台上手持话筒声若洪钟地宣布芦湾每到农历的三、六、九日逢集,热烈欢迎人们前来捧场。
从那以后,每到逢集的日子卖猪肉、卖瓜果、卖蔬菜、卖衣服的商贩们纷纷来做买卖。 十里八村的人们像是一股潮水在集市上汇聚。
集市很小,从南到北一览无余,却分区明晰,菜市、肉市、衣市与牲畜市等一应俱全。 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形容它十分妥帖。
那个时候的集市像是一个婴儿,简陋而小巧。 每到逢集的日子人满为患,促使集市膨胀,兴建很多店铺,饭店、理发店、花圈寿衣店、杂货商店、电器店等像是一朵朵野蘑菇在集市上迅速生长。
集市给村庄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像是一名化妆师,装扮人们的容貌风采,也给人们的思想点染上一抹新颖亮丽的色彩。 故乡自从有了集市,我们的饭桌上有了沿海的虾米、海带与带鱼。
我们能够吃上香蕉、菠萝与柑橘。 姑娘们从集市上买回牛仔裤、发卡和洗发水,打扮得更加漂亮。 到了冬天年轻人穿上了暖和而潇洒的羽绒服,还能够用上录音机与磁带听流行歌曲… …
在我们的生活中,仿佛有一扇未知之门被集市悄然打开。 我们的生活也因此改变。
假如土地是村庄的心脏,河流是村庄的血脉,树木是村庄的肺,那么集市便是村庄的肾脏,它调节村庄与外界交换能量,为村庄输送新的生命力。 二十多年之后,我长大了,已经在城市漂泊很多年。
有一天黄昏我回到故乡,只见夕阳落在地平线上,绛紫色的夕照辉映着远去的河水。 不远处的集市店铺林立,一眼望不到头,此时的集市像是一个青年人,稳健而富足。
我想很多年前它很小的时候,也是我很小的时候。 和过去相比,它变得难以辨认;假如它像人一样有记忆、有情感,必定能看出我的改变。
万物好像均有命运,在天地间自我修行,与时间搏斗或和谈,有得有失,有进有退,有喜有悲,构成命运的曲线。 我独自坐在河岸上,望着安静平和的集市,望着余晖笼罩的故乡。
夕阳渐渐坠落,霞光渐渐黯淡。 在夜色弥漫中集市上亮起一盏盏灯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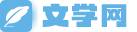 文学网
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