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成…. 喊声不知从哪冒了出来,紧接着布拉听到了身后不怀好意的笑声。 走在村路上的她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她没有回头,她不想看那人是谁,她只是侧在一旁往怀里拉紧了东吉。 自从那个与自己同名同姓的农民上了星光大道之后,睡在户口本里多年的这三个字就时不时被人拎出来,有意无意地丢在她面前。
她当然知道他们是拿她开涮逗闷子。 对于这些有意的揶揄、嘲讽她从来都保持沉默。
这些年如果说是习惯了,莫不如说是她用最大的坚忍给自己的心间铸起了一堵墙,那堵墙在岁月里已经刀枪不入风雨不侵。 尽管在夜半那堵墙会突然坍塌… …
布拉听出是谁了。 她用左手抚了下长发,再用中指挑了把它们重新挂在耳朵上。
整个一张脸,不,一个大大的口罩露了出来。 这个时节街上已经没有人戴口罩了,而布拉不同。
口罩是她身体的一部分,摘下,不亚于扒层皮。 东吉抬起小脸,看着妈妈。
她不知道妈妈怎么还有这样一个名字。 聪明的她已经从妈妈的表情里知道了什么。
她愠怒地瞪了那人一眼。 然后本能地靠近了妈妈。 好好走,别踢着… …
布拉叮嘱女儿。 东吉今天穿了新皮鞋,那是布拉用边角余料做的。
东吉老早就向往了。 因为妈妈说了,只有到镇上的时候才可以穿。
她盼着新鞋,更盼着去镇上。 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分外地神圣的了。
那些日子她每天趴在妈妈身旁,一眨不眨地看妈妈上帮,定形,下楦。 终于等到了昨天,她急不可耐地把鞋子套在脚上,一掀一掀透着十足的得意。
今早出来的时候,她依然把腿抬得高高的。 东吉嗯了声。
那人脸上讪讪的。 布拉有意放慢了脚步,让那人走过去。
这时她下意识地摸了下口袋里的户口本,身份证。 可别忘带了,这可决定着东吉的命运。
虽然那样轻,那样薄,不过一张纸。 对于布拉,却是身家性命。
累不累,妈妈抱啊—— 东吉就势耍赖了,张开双臂,布拉迎合着她。 一团胖乎乎的带着温度的肉黏糕似地贴紧了她,布拉用戴着口罩的脸狠狠地蹭着她。
东吉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东吉,你说,妈今天办事儿顺利不?
顺利! 东吉不假思索地回答。
她知道妈妈和她一样。 对于今天准备了好久。
今天早上又是洗头又是找新衣服的,怎么能不顺利呢? 对于活动范围只在院子里和屋子之间的东吉来说,她当然不知道顺利与不顺利意味着什么。
户口本上这样写着布拉的身份: 长女:刘大成,性别:女,出生年月:1958年5月28日。 刘大成三个字有些模糊,有明显的擦痕。
下面有“刘霞”两个字,是用铅笔写上去的,又用橡皮蹭了。 不过这两个字依稀可辨。
臭驴头村上了岁数的人依然记得,布拉出生时,小粉婆子当时就吓傻了。 她接生了浑江两岸数不清的了满族后生,没见过这样的婴孩。
后来村里人说,刘家祖上一定是得罪了天神,要不怎么让一个女孩带着一脸的红肉瘤出来。 据说她爹一下也傻了,跪在院子里张开嘴干嚎起来。 他怎么也不相信,婚后数年无子的他天天上香祷告终于让妻子开了怀,没想到,竟然是盼来这么一个红脸鬼… …
他哭了一会猛然用袖子抹了泪,冲进里屋一把抓住了布拉的脚。 布拉的奶奶此刻也正在坐在北炕呜呜放声,她用了平生最敏捷的一个转身,薅了刘贵,好歹是条命,当狗养吧… …
后来她一直没有名字,白旗后裔的奶奶把她唤作布拉。 布拉是满语荆棘的意思。 意为这孩子扎手,让天神以后多让让路给她… …
她还没记事,奶奶就走了。 布拉好几岁了,没有正式名字,也没有上户口。
那年还是和二成一起上了。 管登记的老孙头问这孩子叫什么名。
他爹随口说,刘大成。 老孙头一愣:一个女孩,叫这名?
爹不耐烦了,有个名就成了,还指望着她成龙成凤? 这个名字还是跟二成借光哩。
后来她知道,爹怕弟弟有个闪失,一定要把她和弟弟的名字绑定。 如果弟弟叫二龙,她一定会唤作大龙,如果弟弟叫二福,那她一定就是大福。
她的童年是万般小心的,避人的。 她早早地从人们的惊讶的目光里知道自己是个“鬼”。
娘把家里的镜子都藏了起来,她是在小河里认识自己的。 她只看了一眼,就趴在河岸上哭了起来。
那一刻,她着实把自己吓倒了。 终于明白小伙伴为什么要躲着自己,为什么有人故意到她家来,原来就是想看一眼村子里有名的鬼… …
她小小的身体在大石头上不停地抖,眼泪流到嘴里,很苦很涩。 谁家的女孩整个脸是这种黑紫色? 还有大小不等的肉疙瘩分布在上面… …
哪怕缺眼睛,缺耳朵也就罢了。 为什么,自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
七八岁的时候,她用毛巾给自己缝了个大口罩。 眼睛以下的部位掩盖得严严实实的,从那时起口罩和她就不分开了。
那年,娘送她上学,老师安排她和一个男生坐在一起。 那男生知道她是传说中的“鬼”,像受惊吓的老鼠样,立即跑了出去。
老师没法儿,又安排了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当时就哭了,仿佛受了莫大的委屈。 布拉还看到男生女生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她的头轰轰的,她害怕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刻她真的永远不打算再睁开了。
老师只好劝娘把她领回家。 娘在路上早就准备好了一肚子的请求,这一点,布拉分分外清楚。
娘讨好的脸看着老师,她扯了娘的衣襟,力气大得很,娘差一点跌倒。 娘看着那双泪眼,明白了。
记得爹在饭桌上“啪”地撂了筷子,嘴里的饭没来得及咽下,她觉得空气里迷漫着爹的喘息,差不多要把房子吹倒。 爹觉得她给家里丢尽了脸。
对于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爹是看透了。 她躲在娘身后,像秋天里瑟瑟的一片叶子。
这时娘又搬出那句话。 他爹,记得她奶奶的话,千万别把她当狗往外撵,临终前,你答应的了… …
啊,你别气着。 娘的脸哭皱成一团,菜帮子一样难看。
别看娘低三下四的,在布拉的记忆里,不管爹怎样咆哮,娘的哭声和哀求同队上的嗽叭一样,不管声音多大,只要开启,立马会让爹止住。 直到许多年以后,她理解了爹。
渐渐地,她知道户口本上的刘大成三个字就是自己在重要场合的正式指代, 她像第一次认识自己的模样一样,躲在柴垛后再一次泣不成声。 相比之下,二成就显得格外金贵了。
二成上小学的时候,爹给她的任务是护送二成上下学。 她心疼二成,就让弟弟在自己背上。
二成不爱学习,就让姐姐代他写作业。 她向往的课堂就从野地里开始,二成上了三年,她读了三年。
二成读了五年,她也读了五年。 她认得字比二成多,乘除法也比二成算得快。
后来,二成说什么也不读书了,布拉的“学生生涯”也戛然而止。 爹无意间从二成班主任那里得到对布拉的预期:这孩子脑子好使,她要读书,将来一定会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 不念书太可惜了… …
这话一定让大字不识几个字的爹绝处逢生了。 然后爹让十几岁的布拉再去读书,倒是她说什么也不肯了。 唉——这副样子,不指望了… …
就是将来出息了,哪个官饭里(单位)敢留? 爹背着手,每一个字咬得狠狠的,仿佛要嚼碎她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后来爹放出狠话,让她去挑大粪,砍大柴。 爹的用意是要用歹毒的方式作为她忤逆自己心愿的一种惩罚。
娘心疼她,怕真那样。 偷偷地把家里两瓶“大源泉”送给了队长,让队长一定派个轻巧活。
队长瞟着娘,又看着细细弱弱的她,最后表现出无限的大度:就这个没追上肥的小茄子顶半拉人吧! 也算咱没歧视妇女。
就这样,队长把她安排在女人堆里,拔苗,看青。 她珍惜上工的每一天。
认真地完成每一份使命,她想用汗水换来意外的眼光和赞赏,却是徒劳。 依然有人用眼乜斜着她,躲着她。
特别是那些害喜的,要娶亲的,张罗上梁的,仿佛靠近了她,就接近了一枚小炸弹,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的好事炸得灰飞烟灭。 这一点,她懂。
当然也有好心的女人凑近了她,小声地问她身上来没来那个? 胸口鼓没鼓?
她不回答。 以不变应万变,她不记得是从哪里看到的这句话。
反正她告诉自己,不作声,不作声。 还别说,这一遭真管用,时间久了,别人还真把她当成了不会说话的小哑巴。
她多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刘霞刘燕刘红,只要不是刘大成任何一个女伢的名都行。 那个雨天趁歇晌,她战战兢兢地来到队长家。
对于这个平日里看不见脸的女伢子队长亲切地接见了她,大有一种为她撑腰掌舵的架势。 当队长听懂了大口罩背后断断续续的请求,他眨着眼睛看了她半天,觉得这问题太小了,小到没必要他亲自出面。
只丢下无限温柔的一句:找老孙头去。 那可不行,你这名字是你给爹起的,跟二成是连带关系… …
你闹玩儿哪。 再说了,你不是叫布拉吗?
有谁唤你大名? 老孙头一口气说完,见她还不走,去去去——撵狗一样的。
她有些急了,扯着老孙头的衣袖,那就求求你,把户口里的这个名字划去吧。 你这伢崽,说得简单,划去? 那就等于你不在世了,在咱们中国这土地上,就不存在你这个社会主义新社员了,那我责任可大了去了… …
再说,我还要考虑到你的将来。 老孙头把蓑衣往上颠了颠,十分气派地教育着她。 她的头重新低到脖子里,脸憋得通红,费力地挤出几个字:我将来,我将来,我没有将来的… …
老孙头愣愣的,过了一会大笑了起来。 她吓坏了。 好半天,老孙头带着丝丝的长音缓了过来,身体还不停地笑抖:你怎么没有将来,你要嫁人,要生娃的,这个不由你说了算… …
她脸更红了,逃也似地离开了老孙头家。 若干年后人口普查时,布拉曾请求过普查员把刘大成三个字改了。
那个普查员眼睛眨了眨:那赵大胆(队长)都没改,我敢改? 娘俩来到了镇派出所的时候,门上还睡着一把锁。
昨夜的霜一定很重,那锁裹着一层白。 布拉一眨不眨地向路口张望着,张望着,唯恐眨一下之后漏掉什么。
东吉高兴,拍着小手看着街上的车。 布拉怕她没耐心,让她数过往车辆。
东吉数着数着,半天没有车了。 她就把目光停在饭店门口。
一个棕红色头发女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卸门板。 那片棕红在晨光里一晃一晃,东吉只在电视里见过长这种头发的女人,她目不转睛地看着。 妈妈,你也弄成这样的头发,一定好看… …
东吉指给妈妈看。 那个女人听到了什么,慵懒地朝这边看。
布拉一把拦下了东吉,数到多少了? 看,又过来一辆。
东吉早忘了刚才数到哪了。 她的目光又被出摊的小贩拽过去了,那上面有那么多花花绿绿的东西。
布拉正要用包里的吃食来换取东吉的注意力,却见丁字路口终于走来了小戴。 别说话,看,来人了,听话… …
布拉一阵兴奋。 小戴胖胖的,其实并没有多远的距离,却怎么也不见她靠近。
显然,她是看到布拉了,虽见她加快了手臂的摇摆,却依然没有速度。 布拉摸了摸包里的东西,确信它们一一都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周围立刻扑出一片白。
终于走近了。 小戴伸出同样白白胖胖的手,掏出钥匙伸进锁孔。
咔嚓,门开了。 布拉讨好地帮着扶住门。
这么早你就来了啊! 是不是等了很长时间… … 上次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不是我们一个部门的事,我这真的办不了啊… …
求求你,你看我女儿眼瞅着就要上学了,没有户口怎么行? 布拉的声音很小。
东吉看着妈妈。 又看着小戴。
她不知道户口是什么东西。 但她从妈妈的表情里知道,这是天底下最大的事。
小戴没有说话,进了屋直接开了窗子,一股冷气乘虚而入,布拉打了个冷战,接着头发被风吹起来。 布拉终于挺一个劳力了,终于赢得了爹的笑容。 这时她的身材已经分出高山低谷,上工时几个妇女对着她的背影叽叽喳喳的,有人说,看布拉这样的好身板进门就能生小子;还有人说,谁知道生下的孩子会不会也是个红脸的… …
那年她17岁,喜欢听一个人的口哨,那人的口哨响,脆。 更像小刀一样划过她的腔子,让她心尖儿疼,让她鼻孔酸。
她出勤更早,为的就是在山路上远远地看那人一眼。 他叫陈喜子,负责放蚕。
枪打得准,队上的那几个漂亮姑娘都吃到他的雀肉。 她从未近距离地看过他,一是她不敢,二是她怕惊扰了他。
就像枝头上落着一只好看的画眉,远远地看着,听着就足够了。 陈喜子同其他人一样,瞅都不瞅她一眼。 她觉得自己还不如桑树上的一只死蚕… …
刘家没有像其他有女儿家的那样种骄傲,相反却在夜里出现了爹的叹息。 那天,她无意间听到了爹和娘的对话。 爹说也不知道后山的王瘸子能不能看上她,要是看不上的话,还得托人… …
咱家拿什么打人情? 娘说,要不再等等,布拉还小。 爹说,再过几年她就二十了,你想让她臭在家里了… …
爹说得咬牙切齿,仿佛她已经臭了。 娘不再说话,只有喘息,也可能在掉泪。 她的眼前闪过后山的王瘸子,傻愣愣的眼神,豁牙的嘴里时不时往外淌口水… …
她一阵恶心。 爹不是说了,就这样的,还不一定能看上她… … 那就是说,还有更差的,把她推给还不如王瘸子的男人… …
她只和这类男人搭配。 她的心一阵抽搐。
那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布拉偷偷地起来了。 她先在自己的房间里磨起了剪子。
她怕自己犹豫、贪生。 为了不给自己留半点退路,她对着窗外咔嚓地剪掉了心爱的长发,而且只剪了一半。
然后摸到了那瓶敌敌畏。 那是娘准备药跳蚤用的。
事先她早早地瞄好了,喝完后她默默地走出院子,然后回头看着自己的家。 爹和娘,我走了,我去找奶奶了… … 二成,你要听话… …
对于这一天,她从听到爹和娘说话那天就蓄意准备了。 她不能死在家里,那样会影响二成的名声,也不能在上工时服药,那样很快就会被人们及时发现… … 总之,一定要夜里实施自己的计划,等到第二天人们发现她的时候,不过是一具可怕的死尸… …
那就无所谓了。 这一刻如此轻松,她从未如此大方地对着天与地,村庄,小路。
她的心头涌出一阵阵惬意。 甚至有了歌唱的冲动。
她真的唱了起来:雪山啊闪银光,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革命道路多宽广—— 走着唱着,唱着走着,而且她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 不知是谁家的一只狗先叫了起来,不一会全村的狗都跟着叫了起来,在她脚步穿过的地方指挥似的集体和着。
她慌乱起来,接着没有目的地跑了起来,像极力挣脱什么。 外面的月光白昼一样,把一个张牙舞爪的影子夸张地复印下来。
先是娘醒了,发现她不见了,然后快速地推醒了爹,还有二成。 他们顺着狗叫的方向追赶,一家人高低不等的影子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规模。
所到之处,鸡醒了,人醒了,整个村子都惊醒了。 事后有人说,那天村子里异样得很,月色空前地好,很多人都没有睡沉。
她在惊慌之中几步窜到了大坝上。 她不知道药性为什么还没发作,她等着,并在心里焦急地对天神说,快点快点,让我清清静静地死去,我是下了大决心的,绝不活着,求你了,天神… … 快… …
大坝刚刚完工,还没有正式使用。 这几天,队里正在排练秧歌迎接竣工剪彩。
她站在那里,出奇地安静,没戴口罩,挺直着胸,她终于可以如此坦然地面对一切。 队长傻了,爹也傻了。
这个小茄子竟敢这样? 布拉站在那里,腰杆相当地挺,眼神相当地平静,完全没把队长,不,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爹,我不嫁人,你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跳下去,让我变成水… … 让一切都不存在—— … …
这个红脸鬼竟然这么张狂? 队长狐疑地看着坝上的她,不知怎么,突然觉得她是只怪兽。
莫非真是狐妖鬼怪附体了? 这一想不要紧,队长立刻腿软了。 他听说那些年死去的“牛鬼蛇神”变着法的回到人间,一一来找仇人算帐… …
想到这儿,他的脊骨里咕咚咕咚地往外冒冷气,他抽噎了下。 啊呀——刘贵啊,你快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要答应她啊,可不能让她在这个坝上出意外啊。 多好的闺女啊… … 刘大成,啊不,布拉,你快下来吧… … 下来吧,不能啊… …
让我死,让我清清静静地死。 就像山上的映山红,静静地开,静静地落,一辈子都不招惹谁,我求你,死神,天神,快点来啊快点啊——她在喃喃地说着,在别人听来,从来不怎么说话的她此刻一定是鬼魂附体了,你听听那词,怎么就跟广播里说的似的。
坝下的人你看我我看你,那眼神分明是看到鬼才有的。 布拉晃了下头,只觉得脑袋一边沉一边轻。
没有头发的一边露着头皮,一定向秃岭山一样,她不敢想有多么恶心。 她意识到死神没有来,她真的不能等待了,不能了,只有跳下去,化成水,才能逃过这一切。
你看那水多么轻松自在,没黑没白地唱着。 想什么时候青,就青着,什么时候蓝,就蓝着… …
队长扯开锣一样嗓子重复着,她听不到队长的话了,她觉得这一刻真是好玩。 队长竟然也能这样低三下四地求她。
不过她知道队长并不会在乎她跳不跳,而是怕影响了臭驴头村的名声、他队长的名声。 今天我要让你们看看… … 作者:冯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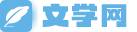 文学网
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