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踮起了脚… …
叶明国身上肮脏的气味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瞬间袭击了她,接着她的双臂被叶明国死死地钳住。 星光也在眼前?
怎么不是平日里仰头看的那种? 怎么在脚下乱转… … 若干年后的叶明国到布拉家买挂钱,依然一副功臣状:要不是我,你早喂鱼了… … 操,那个龟孙儿赵树森,答应我两瓶酒的,到他死我也没看见… … 原来,那瓶敌敌畏早就用完了,娘在那个瓶子里继续灌满了水,想借那点药性再做其它用途… …
就从那天起爹不敢把她轻易许人了,好像也就是从那天起,人们也不敢再嘲笑她了。 尽管村里人时不时地把她和鬼怪扯到一起,可她不管这些,甚至比平时更挺直了胸,高昂着头,爱谁谁的样子… …
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发现她的眼神里仿佛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意味。 人们真的重新认识她了。
她觉得,这一切是拿自己的命换来的。 就在那一年,陈喜子结婚了,听说老丈人家没男孩,只要陈喜子肯做上门女婿,人家不要一分钱彩礼。
这对于一窝小子的陈家来说,自然是欣喜万状。 那天一辆蓝卡车挂着大红花开走的时候,布拉在山头上远远地看着,并顺着杠梁追了很远,直到喜车拐出了她的视线… …
然后她把那个织好的白围领挂在树枝上。 那是在歇工时偷偷给他织的,拆了织织了拆,完成的时候她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以后再不用小心的保管了。 她看着树枝上的随风飘摇的围领,自言自语。
喜子极少回来,每每人们议论的时候,布拉都恨不得再长出两只耳朵。 有时,她的梦里还时常出现一阵欢快的鸟叫… …
后来生产队解体了,爹妈也先后过世了。 二成成亲后,和她分了家。
为了生计,她学会了剪纸、刻挂钱。 这两件事多么美啊,特别挂钱,和对联一样的,哪家的门上少得。
每年的下半年她就忙开了。 那些红红绿绿的纸铺在炕上,经她细心地画,刻,那些龙啊,凤啊什么的就活灵活现地舞起来,再配上年年有余,步 步登高的字眼,她不出门手艺就飞到了各村。
一到腊月她家的门口就出奇地热闹。 有的小贩可怜她,常在背地里多塞给她几张票子,当然她不声张的,等人家再来时,她也多给人家一些挂钱。
渐渐地,她喜欢用刻刀在纸行走,仿佛这种方式是她的另外一种表达。 没人的时候,她摘下口罩望着窗外,眼前有鸟,有河,有树,都那么鲜灵灵地,她觉得日子真好… …
那年腊月,布拉看到了一张旧报纸。 上面一则广告吸引了她,是去除太田痣的。
她当即无法自制,以至于拿报纸的食指和拇指一门地哆嗦,奏出了她的紧张和心跳。 她慢慢地抚平那张报纸,然后把它镶在镜框里。
累了的时候,就看上一眼。 东吉见妈妈的表情有点为难,她不安地把目光投向了小戴。 我理解你的,可是你手里什么都没有,我真的落不了… … 那天我不是告诉你先到村里开个证明,一是证明你是单身,二是证明你有抚养能力… …
小戴看了东吉一眼,然后拽过布拉小声地说,怎么也得一步步来。 你两手空空,我无法给你办的?
布拉突然想起,上次小戴是这么交待了,我怎么给忘了。 看来真是老了,这样健忘。
布拉自责着。 这时她突然感觉眼里落进了什么东西,不由得掏出手绢擦着。
这时的东吉以为妈妈哭了,是被眼前这个 “官”样的女人欺侮了,突然间她用极快的速度奔向了小戴,然后张开嘴朝一下子叮住了小戴的手。 布拉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听小戴发出了惊惶的哎——哟 东吉没有松口的意思,她咬得极其用心,小脸涨成了紫色。
布拉吓坏了,她没想到东吉会这样。 布拉薅下了东吉,东吉还有反扑上去的意思。
布拉死死地拽住了。 东吉,咱不能这样… … 你要听话… …
布拉忙向小戴道歉。 没什么没什么,这孩子跟你真没得说… …
小戴喘息着并揉着手背。 布拉不知怎的,不争气的泪极速地掉下来。 小戴边揉着手背边继续:这孩子以为我为难你… …
别哭了,在孩子面前不好。 布拉点了下头。 办完这些后,还要找个证人,证明这孩子确实是捡来的,再到派出所报案,办捡拾手续,然后在报上公示100天… … 布拉惊讶地瞪着眼睛… …
东吉看着妈妈,像只受伤的鸟。 小戴继续,这事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拐卖儿童的太多了,为了以后不必要的麻烦,必须要走这个流程,还有,办完这些之后,最后才是到我这… …
此刻的东吉瞪着眼睛看着妈妈,像不认识似的。 因为她从这个女警官诉说的流程里已经清楚了自己的大概。 妈妈—— 东吉,妈妈… … 妈妈给别人办点事… … 来这里打听的… … 不是你的事… … 和你没关系的… …
布拉对着东吉惊愕的眼神说。 东吉死死地扯着妈妈的衣角,唯恐一松手,妈妈就不见了。
布拉杵在那里,有些糊涂,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要跑多长时间。 她记得那年管户籍的要她到民政局。
她去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接待了她。 他看过户口本后,不停地打量着她,那目光是从头碾到脚,接着又从脚碾到头。 布拉只觉得 一阵阵轰隆隆的声音把自己压成了饼,自己轻飘飘的,后来竟不知自己是怎么飞出来的… … 这些年,她最打怵的就是见人… …
她不知道跑完这些需要多长时间? 到秋天时能不能耽误孩子入学?
她愣愣地站着,大有不知何去何从的意思。 小戴看出来了,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帮你跑… … 谢谢小戴,你这样好… … 你多不容易,带着孩子… … 布拉听了这话,哽咽着,我可要好好地谢谢你… …
布拉那些年已经积攒了不小的一笔钱。 那年春天她一人去了省城的大医院,咨询之后,布拉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的。
反正那双脚如同陷入淤泥里,每拔出一步,分外吃力。 她笑了下,当然是嘲笑自己。
活了这么多年,她一直生活在别人的嘲笑里。 这回她嘲笑了下自己:你以为自己是富翁了,离自己的愿望不远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
她怎么都没想到这些年的血汗,还不够手术费的一个零头。 她逃似的赶到了火车站。
她顿时觉得浑身没有一丁点力气。 她捡了一张小广告,铺在地上,然后盘腿坐到上面。
她一会像笑一会像哭,反正眼里又是泪又是汗。 一个男人的目光停在她的头上。
是她的长发吸引了他。 凭着经验,眼前这个女人一定是乡下来的。
城里人不会这样坐着。 还有她的外衣,只有乡下女人才穿着这种过时的红毛衣。
他转到了布拉的正面,想看看她的脸。 他很失望。
女人戴着超大的口罩。 不过,也让他很大胆。
凭他的经验,这类女人没出过门,更没见过什么世面,爱小,容易得手。 30元行不?
对于突然间站在眼前的这个人,布拉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或是觉得他在跟别人搭讪。
她把左腿抽出来压到右腿上,换了个姿势。 男人俯下身继续小声:30元,小旅店,十分钟完事,还管饭。
男人四下看了看,并把手里没有商标的半瓶矿泉水讨好地递给她。 她终于从他淫邪的小眼睛里明白了什么。
去***的,不要脸的臭叫驴,——你再说一遍——我撕了你。 布拉突地站了起来,并把那只肮脏的手用力推开。
她的声音太大了,太大了,以至于把周围的嘈杂都压下去了。 她没费力就拽过周围人的目光,人们诧异地打量着她。
她冲着那个男人继续嚎叫着,尽管声音在口罩下有些瓮声瓮气,还是把一个警察引来了。 那个男人老鼠一样快速挤到人堆里。
消失了。 布拉回家的当晚,把镜框里的那张报纸掏出来,她觉得都没怎么碰,就化成屑了… …
纸就是纸,她说。 那一年腊月,天嘎巴嘎巴地冷。
布拉傍晚时在柴垛里发现了一只狐狸,那只狐狸没有立刻逃开,而是用可怜的目光看着布拉。 布拉俯身把它抱了起来,觉得它轻得像一团棉絮。
在这样的大雪天它是找不到任何吃食的。 布拉有些激动,它能投身到她的门下求救,就把她看得高贵。
她在那一瞬间觉得自己神圣而不卑微。 村子里的人怕了,特别是那两个早对布拉觊觎以久的老光棍,他们不再相互打探,也不再说关了灯,谁还在乎脸那样的话,而是说布拉真的是狐狸转世。
敢 把狐狸抱到自家屋里,何况还是怀孕的母狐狸。 她和那些鬼狐狼仙不就是一路货色么?
趁着还没把她咋地,快打住吧。 这要是招惹了她,还说不定自已要遭多大的殃。 很快,村子也传出了这个红脸鬼作妖的话,听说布拉把过年的肉都给狐狸啃了,还有人说夜半里她的房间传出说话声,笑声… …
转年春天,布拉把狐狸和崽子送到了山里,人们说你看吧布拉,说不定你会有什么劫哩。 布拉还是那样沉默着。
恰恰相反,布拉没遭遇到什么劫,却在那年秋天,遇到了东吉。 如果说那天有什么异样的话,那就是她那天特别想穿新衣服,那种感觉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按常人的想法,上山不应该有这种念头。 可是她平日里极少迈出家门。
上山也就是出门了。 再说了,像她这样的人,衣服都是穿给自己看的。
给那些山看,给那些水看。 它们不至于惊讶,更不会嘲笑。
那天她站在石桥上,长久地看自己的影子。 水里的那个人腰身有些塌了。 甚至头上的白发已经占了不小的比例… …
布拉最初看到那个红包裹,是在夕阳里,在她准备下山的时候。 她以为是谁劳作时脱下的红衬衫,或者是谁飘落的红头巾。
她都走到山脚了,无意间抬头,那红还在杠梁上。 她觉得不对了… …
因为她隐约听到了哭声,婴儿的哭声。 她快步地跑过去,是个包裹。
哭声是从包裹里传来的。 她不安地抱起她,一张涨红的小脸正对着她。
不知怎地,布拉一下子就哭了。 她觉得她仿佛是若干年前爹要扔掉的那个自己。
奇怪,她不哭了,那双明亮眼睛一眨不眨,仿佛在这里等布拉好久了。 看着看着,布拉的心头发颤,臂腕里的这个小身体的体温慢慢地传给了她,温润了她,她的身体里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在微冷的秋风里,她觉得自己像一朵迟开的大丽花,一瓣一瓣地打开了,甚至她还闻到了命运里飘来的一股芬芳。 那种感觉和味道令她再也放不下了她了。
事后,她想,如果当时有人把孩子从她手中夺走,她会瞬间枯萎的。 真的,毫不含糊的。
她本能地朝四下里望了望,喊了起来,没有回音,只有风吹过玉米地的沙沙声。 这回声给了她一个明确的答复:四周没有任何人。
不知怎的,她仍然觉得在哪个庄稼地里有双隐匿的眼睛。 她打开包裹,里面板板整整地叠着一张纸,上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着: 刘大成同志:你条件好,心好,孩子你就捡了吧。
没毛病的。 将来绝不会找你事(麻烦)。
我们给你克(磕)头了。 再下面是孩子的生日。
看来她这是被人盯上了。 就是不在路口捡到,这人也会把孩子送到她家门口。
她抱着婴儿,嘴唇哆嗦着,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最后索性把头埋在婴儿的小被子上,泣不成声。
她觉得怀里的孩子才是天下最可怜的,比自己可怜一千倍一万倍。 很快,二成和媳妇来了,劝她不要找累赘。
一个人清手利脚的多好。 养孩子不是养小狗小猫。
你现在都快半百了,自己还需要别人照顾呢,还找那麻烦? 她固执地坚持着,二成在无奈之下搬来了叔和婶。
叔和婶拿出长辈的姿势,更有为她命运担忧和负责的态度。 起初她还耐心地听着,后来东吉哭闹了,她表现出了不耐烦。
别说了,我从抱起她的时候,就没再放下,就这么定了。 将来就是要饭也要养她… … 她太可怜了… … 好好的,就给扔了… …
她说不下去了。 令叔和婶吃惊的不是她的话,而是她抱孩子、喂孩子的姿势和神态,那分明就是自已生了似的… …
以后,她常常去县里的婴儿专卖店,大包小包的,邻居说,不用啊,镇上什么没有,费那个劲。 要买就买最好的,不能亏了孩子… …
她的小院里时不时飘出笑声,人们看见布拉背着那个小孩子,做饭,打水,在案板上刻刻画画。 她不允许东吉饿着,冻着,不以让她有半点的不舒服。
她还变着法地打扮着她。 她觉得上天真对自己真好啊!
让自己清寂的日子有了活气,有了奔头。 那天她做了个梦,好像又回到了队里。
远远地看见陈喜子扛着枪下山了,她怕他在河边洗脸擦背的时候看到陈喜子三个字。 那是她在歇工的时候反复写在石头上的。
她要在他没发现之前赶紧擦掉那三个字,慌乱之中是擦掉了,却单单剩下了一个“东”,后来她又取了“喜”字的一部分,于是东吉就叫出来了。 醒来后,她俯身再看着这个睡熟的小家伙。
她觉这孩子是她和陈喜的,她被那种不可思议的想像包围着,说不出的幸福。 东——吉——东——吉。
终于,东吉五岁的时候她的存折空了。 如果继续她的挂钱生意,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东吉越来越大了,要入学了,要有更多的花费,她真的慌了。 不过,她很快调整了自己,她可以去打工。 她还想好了,还可以去县里做钟点工、力工… … 老天还能饿死瞎家雀… …
终于等到小戴不忙了。 她小声的地央求着,麻烦你,给我写在纸上… … 我,我怕我记不住… …
小戴唰地扯过一张纸,好。 小戴一项项地写着,时不时停下来,想下,再继续。
娘俩走出门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 卖菜的,卖肉的,炸麻花的,蒸馒头的,各种吆喝声混在一起,无比诱人。
东吉拉了妈妈,布拉明白了。 她摸了摸兜里的纸币,告诉自己,怎么也不能太屈着孩子,一年来镇上几回?
给东吉要了麻花还有米粉,布拉说自己不饿。 早上吃得太多了。
东吉跳上小板凳,兴奋地挑着筷子,吃得哧溜哧溜的,小脸不一会热得通红。 东吉终于吃饱了,碗里还有不少汤。
布拉觉得丢掉太可惜了。 她想摘下口罩喝掉,却有几个人在看她,算了。
在商场里,东吉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个绒布熊,布拉问了下价格,然后小声地还了价。 那个胖女人倒大方,零头抹了。
还没等付完钱,东吉一把抱了过来,开心地笑了。 布拉一看墙上的钟,觉得时间不早了,拉了东吉走出来。
布拉真的有些累了,走回去至少还要一个钟头。 干脆,打个三轮。
今夏的雨水把路冲了,大路上坑坑洼洼的,小三轮跑得飞快,布拉抱着东吉,颠得骨头都快散了。 看到村子的时候,脚下的路更不好走,娘俩决定下车。
布拉边走边又掏出小戴写的那张纸,逐一念叨着这些个流程,这其中数捡拾证明最难了。 找谁证明呢?
要不找叶明国。 给他买点好酒… … 还要到报社公示,那岂不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了东吉的身世… …
那记得那个冬天,在东吉一百天的时候,她给村里的每户人家都叩拜过:为了孩子的成长,不要说这孩子是捡来的。 村里人当着她的面都答应了,她走一家感激一家。
半夜回来腰都酸了。 而现在… 她的胸腔里拽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
二成这时骑着自行车不知从哪赶了过来,看到了布拉母子跳下车。 是不是又白跑一趟?
我就说了,这事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 当初怎么劝的你?
二成看了东吉一眼。 东吉知道二叔一直不喜欢自己。
你这才哪到哪,将来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尾哪? 这上学是个一个钱两个钱的事? 将来好了好,不好,嗯… …
你走着瞧吧—— 东吉看着妈妈。 二成,你别说了,当孩子面… … 我能扛过去的… …
二成跨上车把一窜丁当的响声丢在小路上。 东吉突然间站住了,语气里有股气焰飘出,妈,我是不是捡来的?
这一声太突然了,震得布拉一下子不会迈步了。 她蹲下来,与东吉的眼睛对视着,孩子百精百灵的,什么能瞒不住?
莫不如让她知道自己的身世,反正要面对这一切。 这是她小小年纪必须要面对的流程之一啊。 你是捡来的,没错… …
布拉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东吉可怜巴巴地看着布拉,清澈的眼里立刻涌出了一层水气。 你不要怪你的爹妈,他们一定要是有难处了,不对,是他们看我可怜,自己孤零零的,就把你送给了我,好让我有个伴… …
布拉有些语无伦次。 这些不重要,关键我们在一起,不管是不是我生的,还是… … 捡的,只要我们在一起… …
布拉的泪下来了。 东吉心疼了,她猛然抱住了妈妈,我不是捡的,不是捡的——我是你生的,我不是捡的… … 你别把我送回去… … 好吗… … 我怕… … 布拉忍住泪水抱住了东吉,好孩子,不会的… …
我要给你上户口的,那样,我们的命就拴在一起的了,这辈子都不会分开了—— 东吉终于明白了。 妈妈如此看重的东西原来和自己有关。
她深情地把妈妈抱得紧紧的。 人家还没承认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努力。 我们从这里开始… … 布拉拿出那张纸给东吉看,东吉抽泣着,既而哇哇大哭… …
布拉抱住她,不时地安慰着。 这时一阵风吹来,吹走了那张纸,布拉陶醉在自己的喜悦里,她没想到,在她眼里最难的一道槛,竟然这样轻松过了… …
她抱着东吉,心头无比欣慰。 是东吉发现的那张纸飘了起来。
布拉哎呀了一声,她快速地松开东吉,跑着上前抓住那张纸,东吉也跟在妈妈身后。 此时的天边成片成片地红着,像一幅巨大的水粉画。 那红像血,还像春节的红挂钱… …
把稻田、村子都染红了,奔跑的布拉和东吉也被染红了。 作者:冯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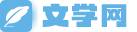 文学网
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