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屋,是藕池河畔一座五间房子的茅草房,土木结构,坐西朝东。 窗户是木格子的,上面糊着暗黄色的麻布纸。
它像一道屏障,无论窗外电闪雷鸣抑或雪花飘舞,窗内都是暖暖的。 黑夜来临,窗户的那头点亮一盏盞灯时,这或明或暗的四方物,总能悄悄染上室内的温馨或忧愁,落在熟悉它的人们的心尖上。
深夜,我一拐进那条小路,第一件事便是看看家里的窗,若是亮灯,再多的心事也会先放下,觉得安稳起来。 清晨,我满怀期待地推开窗户,像拨开满目的愁云般拨开满屋子里晦积了一夜的阴气,惊喜地感受着清淡宜人的气息扑面而来。
阳光柔柔地探过窗子洒到屋里,暖暖地落在我的小脸上,似乎还带着绿植的香味。 透过窗户,放眼望去,挺拔坚韧的香椿树,广阔肥沃的田野,呢喃细语的燕子,叽叽喳喳的麻雀。 长者隐约悠长的吆喝声,还有妙龄女子清脆悦耳的叫喊声… …
一切都是美好而淡雅的样子,这或许便是陶渊明心之向往的桃花源吧! 冬天,地里没了农活,这时老奶奶、小媳妇和少女们最忙碌、最愿意干的事情,就是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纳鞋垫或者摊开五颜六色的纸张,手持一把小剪刀,相互商量着、观摩着剪窗花或鞋垫。
她们把窗花看得很神圣。 谁剪得好,大家都观赏和夸奖;如果剪得差,脸上无光,别人会说她手不灵巧。
那窗花,有飞禽、游鱼、猛兽,有盛开的花朵和饱满的硕果,每一幅都色彩缤纷,栩栩如生,那丰收的喜悦、耕作的欢快、自然的单纯、团聚的祥和,似乎进入了人间仙境。 媒婆说媒,怀里揣着姑娘剪的窗花,到男方家,把窗花一亮,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农村人把剪窗花与做鞋子、过日子直接联系起来。 剪出好窗花,肯定能做出好鞋子;做出好鞋子,才能过出好日子。
冬天,我们家也都贴窗花。 二哥会挑个天气晴好的日子,领着我们把窗户上已经泛黄的窗户纸和窗花一点点撕掉,用鞋刷细心地刷掉窗户格子上的尘土,再用抹布把窗棂擦得一尘不染,然后小心翼翼地用小火熬的黏黏的米糊把麻布纸贴在擦拭一新的窗户上,接着在麻布纸上贴上窗花,屋子里顿时亮堂、喜庆、活跃起来。
站在窗前就能欣赏到一幅美妙的乡村风景画。 晴朗的日子,阳光透过窗户纸照进屋里,窗花在光线的照射下鲜活美丽,给简陋、清贫的农家,带来少有的快乐和活力。
月光皎洁的夜晚,我躺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一缕缕月光照在窗花上。 月儿悄悄将温暖注入我的血脉,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于是,我迷迷糊糊地入睡了。 窗花上的场景还在继续,盛开的腊梅,跳龙门的鲤鱼… …
它们像温婉的明月,落在我的枕上,走进我的梦里。 寒冷的日子,一家人围着一盆火,守着一盏灯,悠闲自在地享受着炉火的温暖。
大人们东家婆媳,西家姑嫂,前村后店的拉家常。 十里八村的陈谷子烂芝麻事,道也道不完。
这时候,母亲便把窗花隐含的那些有趣的励志的民间故事讲给我们听。 一家人,说着笑着,吃着喝着,特别温馨美好,特别富有诗意。
很有围炉夜话的味道,正如汪曾祺老先生所描述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上学以后,我常常因为学习和劳动而起早贪晚。 清晨,母亲总是最早起床,把灯点亮,准备早饭,灯光便从窗口映照到房前屋后。
我的心中也仿佛点燃了一片明亮的灯火,幸福顿时油然而生,笑容往往会漾起在我的嘴角。 晚上,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窗户总是亮着的,母亲坐在灯下边做家务活边盼着等着我回来。
当我远远地看见被灯照亮的窗户时,心里一阵阵温暖一阵阵幸福。 推开门,叫一声妈,母亲便放下手中正在缝补的衣服或正在剪着的窗花,从锅里为我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来。
晚饭后,我就着那豆灯火复习功课。 静谧地灯火下,母亲微笑着陪在我的身边,不时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听我读书,看我写作业,脸上洋溢着一种神奇的幸福。
母亲曾指着窗花对我说:“窗花不撑肚皮,不当棉衣,是个念想,映照着红红火火的好日子!”此刻,窗花映照下的母亲凝重温情,我知道她是祈盼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这老屋,走出双脚插在农田里贫穷苦熬的生活。 那年夏天,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随后,我告别了亲人和朋友,也告别了故乡的格子窗,走过村头,跨过那条伴我成长的藕池河,走向外面更精彩、更广阔的世界。 于是,我成了母亲曾经期盼的“城里人”,不再从那小小的格窗里看世界,而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是,在繁华深处,我还是喜欢用纯净的心灵去欣赏蓝天白云,我还是喜欢用儿时的眼光去看人间百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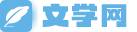 文学网
文学网